天津大學工程碩士研究生馮麗艷的工作是在她的畢業“答辯”現場找到的。“找工作”的過程很簡單——正在她介紹自己的研究時,現場的一位企業總工程師忽然說:“你工作做得這么好,來我們這兒上班吧。”
打動這位總工的并不是馮麗艷的論文有多出色。事實上,那天馮麗艷講解的并不是她的畢業論文,而是一項科研成果。這場“答辯”也不普通,它有一個正式名稱——天津大學專業學位碩士研究生申請學位實踐成果鑒定會。
這樣的“鑒定會”,天津大學今年一共舉辦了10場。包括馮麗艷在內的10名工程碩士研究生憑借自己的實踐成果,不但拿到了學位,還獲得了學校頒發的優秀實踐成果證書。他們也成為國內高校中,首批通過實踐成果獲得工程類碩士專業學位的研究生。
給以后的學生“打個樣兒”
馮麗艷的成果針對自來水廠在水處理的混凝階段,相關藥劑添加量不精確的問題。該成果利用人工智能的自動學習機制和可解釋分析能力,實現了藥量的精準投加,從而幫助企業實現降本增效。
該項目來自馮麗艷導師的一個橫向課題。馮麗艷自2023年6月接手該項目,于2024年12月完成并通過企業驗收。此后,馮麗艷將主要精力放到了畢業論文的寫作上。
然而在今年4月,學校的一紙通知卻改變了馮麗艷的畢業“節奏”——天津大學允許工程類碩士畢業生憑借實踐成果參加畢業答辯,通過答辯者便可以獲得碩士學位。通知還鼓勵有類似成果的學生積極報名。
“作出這個決定并不是我們一時興起,而是基于長期的思考和探索。”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天津大學研究生院學位辦公室主任劉慶嶺說。
據他介紹,早在2023年教育部發布的關于分類培養的指導文件,乃至今年年初正式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法》中,都明確規定研究生可以“通過學位論文答辯或者規定的實踐成果答辯”申請學位。
“2024年,天津大學受教育部相關部門委托,起草工程類碩士生按實踐成果申請學位的具體方案和形式。”劉慶嶺說,最終他們將形式確定為5類,除了專題研究類論文外,還包括調研報告、案例分析報告、產品設計、方案設計等形式。方案交付教育部后,得到了相關部門認可。
接下來,便是實踐了。
今年4月,天津大學決定在今年畢業的工程類碩士研究生中,率先開展憑借實踐成果頒發學位的嘗試,這也就有了改變馮麗艷畢業節奏的那則通知。
“最終,全校共有近20名工程類研究生報名,我們在其中選擇了10名。”劉慶嶺說,“我們希望將他們作為一個‘樣本’,給以后的學生們‘打個樣兒’。”
“你們這樣培養,企業就不用入職后再培養了”
之所以能成為“樣本”,是因為這些學生的實踐項目的確“夠硬”。
“我們選擇的這些學生來自包括環境學院、建工學院、材料學院等在內的不同學院,其成果包括不同形式。”劉慶嶺告訴《中國科學報》,盡管這些成果各不相同,但均有很強的工程實踐價值及很高的技術水準。
按照天津大學的規定,此次參評的實踐成果首先要經過專家鑒定,同時要求參與鑒定的校內外專家中,來自企業以及行業領域的專家不少于一半。只有獲得了這些專家的肯定,項目才能申請進入答辯程序。
作為首個通過鑒定的成果,該校工程碩士研究生鐘行建的方案設計直指航空航天領域。“我的方案通過融合飛機蒙皮智能數據獲取與缺陷檢測算法,為飛機保養維修保證航線安全提供數智賦能。”鐘行建如此介紹自己的方案。經答辯與技術論證,專家組一致認為該方案工程價值突出,具備良好應用前景。
該校碩士研究生鄒豪坤研發的“激光測距仿真設備”也讓鑒定會的專家眼前一亮。“這一設備對提高激光測距系統研發效率具有現實意義。”他介紹說。
該校碩士研究生李闖則聚焦海洋平臺焊接痛點,提出一種基于主被動視覺傳感器的解決方案。該成果已申請發明專利,并在焊接領域重要期刊發表文章……
面對這樣的實踐成果,以及能夠做出這種成果的學生,最高興的是那些來自企業界的評審專家。
天津大學精密儀器與光電子工程學院教授徐德剛是其中一位參評學生的導師。他告訴《中國科學報》,雖然在鑒定過程中,企業專家給學生的課題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但更多是表達一種肯定和欣喜。
“學生的答辯結束后,作為答辯委員會主席的某位企業界人士興奮地告訴我,‘你們如果這樣培養學生的話,我們企業就不用等他們入職后再培養了’。”徐德剛說。
理想狀態:論文占比不超一半
一個看似只是畢業評價方式的變化,實際上牽動著整個工程碩士研究生培養鏈條。
“當前,國內高校在工程類碩士生的培養過程中,學生們做的很多研究直接來自導師的課題,特別是一些橫向類課題。”劉慶嶺表示,國家之所以大力倡導工程碩士研究生的培養,是希望此類研究生能夠直接面向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實際問題,實打實給出解決方案。“工程碩士在實踐類課題方面的參與,正契合了國家的初衷。”
然而,此前工程類研究生仍需通過論文形式獲取學位。這使得無論導師還是學生,在聚焦工程實踐的同時,不得不兼顧論文撰寫。
“很多實踐類項目,是難以用論文形式呈現的。”劉慶嶺打了個比方,這就像一個學徒花幾年時間鉆研包子餡的調制方法,但最終能否出師的標準,卻不是他調的餡是否好吃,而是他能否寫出一篇關于包子餡化學成分的研究論文。
“這是一種明顯的錯位。”劉慶嶺說,正是這種錯位使很多導師難以讓學生專注于實踐項目的研究。
對此,身為導師的徐德剛深以為然。
“在如今的智能時代,研究生教育的重點已經從早期的知識傳授過渡到對學生能力以及思維模式的培養,這一點對于工程類研究生的培養尤其重要。”他舉例說,實際的工程應用領域非常注重研究人員的“節點”意識,以及思維的嚴謹性和系統性,但這些在傳統的高校教育體系中涉及并不多。
“真正鍛煉這種能力的地方就是工程實踐現場,但由于學生的畢業標準只是論文,而不是實踐成果,導致很多導師即便有意讓學生深入實踐,也不得不考慮學生的‘畢業問題’。”徐德剛說。
然而,如果工程類碩士的畢業評價標準以及形式變得多樣,情況便大為不同。
在劉慶嶺的設想中,如果今年的探索能在未來全面推廣,工程類碩士畢業考評中“論文”的占比將降至50%以下,其余學生則可以憑借實踐成果——方案、圖紙、產品等,獲得學位證書。“這應該是一種最理想的狀態。”他說。
在今年天津大學的研究生畢業典禮上,馮麗艷與其他9名研究生成為第一批上臺接受學位證書的學生。同時,他們還獲得了學校頒發的優秀實踐成果證書。臺下掌聲響起的那一刻,劉慶嶺堅信,“未來,能夠收獲這樣掌聲的天津大學學子一定會越來越多”。
《中國科學報》(2025-07-08第4版高教聚焦)本文鏈接:http://www.gxcspki.cn/news-8-5843-0.html沒寫畢業論文,他們卻成了“優秀”
聲明:本網頁內容由互聯網博主自發貢獻,不代表本站觀點,本站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天上不會到餡餅,請大家謹防詐騙!若有侵權等問題請及時與本網聯系,我們將在第一時間刪除處理。

點擊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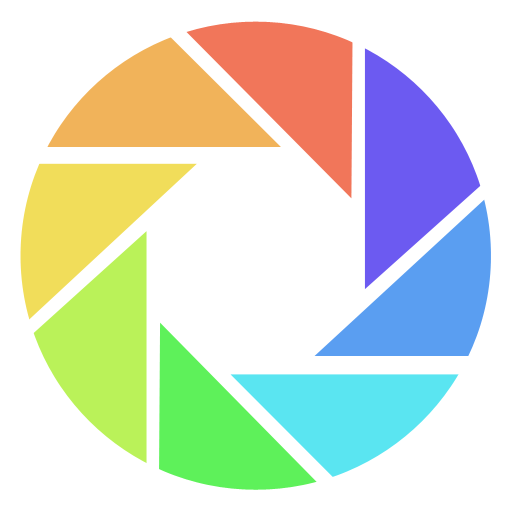 朋友圈
朋友圈

點擊瀏覽器下方“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瀏覽器請點擊“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瀏覽器請點擊“ ”按鈕
”按鈕

點擊右上角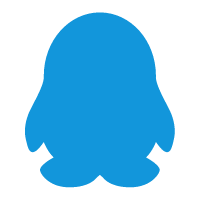 QQ
QQ

點擊瀏覽器下方“ ”分享QQ好友Safari瀏覽器請點擊“
”分享QQ好友Safari瀏覽器請點擊“ ”按鈕
”按鈕
